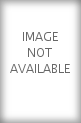*大三下國史大綱讀書會第五週專書報告
李金河這本書著重探討門第婚姻的形成、流變與絕滅,為一縱向的觀察,也兼及橫向的南北比較。要談門第婚姻就先處理門第婚姻形成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基礎,首先需要探討的是士族的形成,他認為士族的形成是在曹魏行九品官人法後才出現的,東漢雖已出現累世為官的情形,但並未含有明確的世襲性,大姓族的政治地位並未確立,所以只能說是一個過渡情況,而不能視為士族的出現;而門第的確立,李金河認為除了九品官人法之外,還必須加上西晉戶調式的成立及國子學的問世,戶調式及國子學為門第提供了經濟及文化上的基礎,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三方面都具備基礎的情形下,門第才會形成牢不可破的社會概念。
李金河分析門第婚姻時,他認為門第婚姻的開始是在西晉,三國時代並未出現門第婚姻,他調查了當時的婚姻狀況,三國皇室並不諱與微賤之人成婚,東漢以來的累世高姓談婚姻時,往往以政治利益為最優先考量,門第上的門當戶對並不是最主要的參考因素;李金河認為西晉時才是門第婚姻成形的階段,司馬氏篡晉,為了鞏固政權而著意與士族聯合,婚姻即是一大方法,但在這時士族還沒有一定要求門第上的門當戶對,寒人還是有可能因為他們各人品貌的出眾而獲得青睞;東晉在李金河的定義下是門第婚姻的凝固時期,這時的門第婚姻做為一種維護血統純粹的排外手段而存在,並被嚴厲執行著,士族只和門戶相當的姓族結婚,並藉此形成穩固的權力結盟,僑姓和吳姓之間並不通婚,國婚也不在門第婚姻中流行,李金河認為門第婚姻的要求下,導致近親婚和異輩婚甚行,在生物基因上劣化士族;南朝政治動盪,寒人上升,士族政治權力下降,開始出現士庶聯姻的情況,也不排斥和門戶不等的士族結合,顯示政治及經濟上的利益已經取代門第做為聯姻的主要考量,甚至因此有些女兒還發出「賣女」的悲鳴,李金河稱呼這樣的婚姻狀況為「士族官宦婚姻」,南朝士族已不排斥和皇室通婚,藉以獲得政治權力,顯示士族已經開始喪失先前的優勢地位,而有依附皇權的態勢;北朝早期士族自矜民族意識與門第,也是群內婚,鮮卑人本身也是盛行群內婚,自孝文帝大力推行漢化後,北方大姓沒有不與皇室通婚的,士族談婚姻時,考量的是彼此政經地位的相等,因此也不排斥和北魏勘定的貴族通婚,以獲取勢力,由於喪失了門第婚姻維護族內血統純粹的原則,因此李金河目這樣的婚姻型態為「民族婚」,尤其北方仕宦時會把婚姻及家世一併列入考量中,就形成了北方大姓崔、盧、李、鄭、王互相聯姻、緊密結合的態勢,門第婚姻便轉型為「士族官宦婚」,到了北周時蘇綽倡議選舉不論家世,更使門第婚的消失起了推波助瀾之勢;總的來看,南北朝近親婚與異輩婚都普遍存在,並且都財賂相尚,又以北方的情形較為嚴重,不過由於北朝會將婚姻列入仕宦的條件中,所以北方尤重嫡庶,南方不但蓄妾成風,也不會特別要求嫡庶,在門第相尚的社會風氣下,譜牒學便十分盛行。
隋文帝將地方官選任僚屬的職權收歸中央、廢九品官人法,行以科舉士制、行均田制及輸籍法、在法律條文上取消了士族的經濟特權,一系列的改革使得士族門戶的經濟、政治特權消失殆盡,但社會上尚門第的風氣仍然存在,故即使隋朝時官宦集團有重新組合過的態勢,新上升的寒門得勢者仍然崇尚與五姓高門聯姻,並以財賂相尚;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盛唐都是如此,儘管唐太宗定《氏族志》具有壓抑士族的積極意義,他本人在安排子弟婚姻時,仍然不脫尚門第的社會風氣,而武則天編顯慶《姓氏錄》的動機,更顯示出在尚門第的風氣影響下,將新興的寒人擠入傳統士族圈子中,而將「后族」提升至第一等的位子,一直到盛唐時期,皇室及武則天的后族都有標榜門第,並試圖將隴西李氏的門第提高,表示當時儘管士族已經喪失了政治及經濟上面的優勢,在傳統唐人的心態上仍然是重視高門大族的,甚至以不娶五姓女為憾,一直要到安史之亂後,關東士族被蹂躙殆盡,南逃的大族無力回天,崇尚士族門第的婚姻才自歷史上匿跡。
李金河以婚姻的性質為主體考察近四百年的流變,採用的資料亦不唯傳統文獻,新出土的墓誌銘也會採用,主要是以統計製表的方式來看婚姻的類型及所佔的比例,從數字上觀察變化,不過李金河並未在一開始時明白告訴讀者他所定義的「士族」及「寒門」,要再去做資料比對是不是能得到同樣的統計數字並不是那麼的肯定,再者「寒門」在書中所指涉的範圍有時是一般平民,有時卻似指較低等的士族,會令人有混淆之感;再來李金河為了表示各時期婚姻性質的不同,而創造了很多獨特的語彚來表示,諸如「士族官宦婚」、「民族婚」、「新士族官宦婚」,在他定義下的「門第婚姻」係指一種為了鞏固政經勢力而試圖維持血統純粹的婚姻,所以只要打破血統的界限他一律視為不同的婚姻形式,換言之,在「門第婚姻」上,他的要求是比日本學者提出的「身份內婚制」要再嚴格的,只是考察這麼細緻的差別後,有必要將每一期的婚姻型態視為不同的型態嗎?這樣的分法難道不會產生矛盾嗎?尤其是他仍然把唐朝的「新士族官宦婚」的結束視為「婚姻不問閥閱」的終點,表示其實這樣的婚姻仍矜尚門第,換言之,將「門第婚姻」的定義縮成這麼狹窄而限制性的範圍是否妥當,是我認為應該再做考量的。
-----------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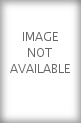
------------
旨彥(彥慈).2005/10/23